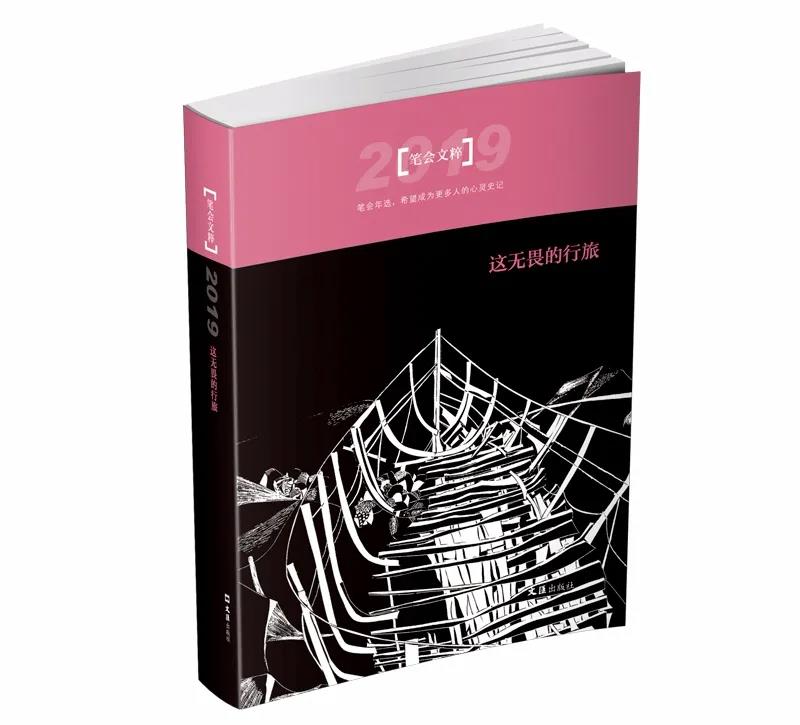https://mp.weixin.qq.com/s/UismYe9mOPZEgfNpE045aQ
忆徐中玉先生二三事 | 谭帆
原创 谭帆 文汇笔会 今天
徐中玉先生(1915—2019)
徐中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想写点什么,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切入口。我与徐先生的接触相对多一些,1983年读研究生,徐先生和齐森华先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1986年留校工作后,一直得到徐先生的关心,以后担任徐先生创办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接手他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可以说,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工作大多是在徐先生的影响下进行的,对他有许多感性的印象,而把这些感性的东西写出来,或许能看到徐先生的另一种“面相”。
一、“看”徐先生抽烟
徐先生是抽烟的,而且烟龄很长,我印象中一直要抽到95岁以后,可见“吸烟有害健康”在徐先生那里是不存在的。1983年9月,徐先生给我们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每周照例有半天时间,上课地点在徐先生师大二村的家里。上课内容没什么特别,印象中讲过《文心雕龙》,讲过《诗品》,也讲过《艺概》,具体内容已经淡忘,讲课形式以谈话为主,也没留下特别的印象。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看”徐先生抽烟。当时一起听课的是陆炜、谢柏梁和我,三人中,谢柏梁不抽烟;陆炜年纪比我们大好多,又在部队当过兵,是一位十足的“老枪”;我也抽烟,但不多。徐先生半天上课,抽烟应该有五到六支,我们当然不敢抽,“看”着徐先生一根根地抽,真盼着早点下课,尤其是陆炜,更是抓耳挠腮,但徐先生上课非但中间不休息,且基本都要拖堂。后来慢慢习惯了,“看”徐先生抽烟也看出点门道来:我们发现,徐先生的点烟姿势特别漂亮,当时抽烟还不兴用打火机,都是火柴,一般用火柴点烟是左手拿火柴盒,右手拿根火柴擦,徐先生也是这样,但特异的是,常人擦火的右手是手心朝下,徐先生擦火却是手心朝上的倒擦,短暂而有力,形式感特别强,且一般要两到三次,非常帅气,也非常大气。这个发现倒也减少了我们“看”徐先生抽烟时犯烟瘾的窘迫,就当审美吧!课后我与陆炜常常聊起这个动作,也尝试用这个动作点烟,遗憾的是总也出不来徐先生点烟的状态和境界,可见先生就是先生,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上课时默默地“看”徐先生抽烟,用审美的眼光看徐先生点烟,倒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课堂氛围,所以上课内容不重要,形式氛围是关键。据说,我们的这种课堂氛围被后来的张建永和吴炫他们一帮“土匪”(建永兄是湘西人,自称“土匪”)给打乱了,他们上课时,徐先生抽,他们也抽,徐先生不抽,他们更抽,而且除李裴外,朱桦、谭运长都是高手,课堂简直就是“乌烟瘴气”。
徐中玉、钱谷融二老与弟子合影
从抽烟的角度看,我与徐先生的关系有几个“层级”:“看”徐先生抽烟当然是最低的层级;1986年留校工作后,可能徐先生以为我也是老师了,每次到他家总会客气地问我要不要抽支烟,我假装客气一下就接过徐先生的香烟,这是第二层级;再发展下去,我已跟那帮“土匪”一样了,徐先生不抽我也照样堂而皇之地抽,这是第三层级;最高层级是在徐先生95岁以后,那时先生已不抽烟了,我经常接到他的来电:“谭帆同志,你到我家来一次。”常常是他把别人送他的烟转赠给我,有时烟还挺多,他会加一句:“你跟老方(指方克强)分分吧。”
徐先生抽烟时间很长,经常会有家人、学生等劝阻他,先生一笑了之,淡淡的一句“我抽烟不吸进去的,都喷掉的”,把吸烟的害处给搪塞过去,但吸烟的人都知道,吸烟哪有一点也不吸进去的,一点不吸进去还能叫吸烟?其实只能骗骗那些不抽烟的“烟盲”。
二、“陪”徐先生出差
作为学生,尤其是留校工作的学生,“陪”老师出差应该是常有的事。对老师尤其是年长的老师而言,有个学生在身边是一种照顾,而对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提携”,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去参加学术会议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学术上的长进,也能积累一些人脉。我“陪”徐先生出差的机会不多,一者,徐先生身体一直硬朗,二来我长期在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和古代小说领域做研究,与徐先生共同出席的会议不多。所以有限的几次机会都与大学语文有关,其中有两次会议给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参加2004年4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国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以陪同身份与徐先生一起参加会议,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毕竟徐先生已九十高龄。会议安排在武汉大学校内的珞珈山庄,环境非常清幽,到武汉大学报到时,我特地要求主办方给徐先生安排一个双人间,我与徐先生住在一起比较放心。三天的会议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所谓“照顾”身份完全成了摆设,先是晚上洗漱后聊天,快到十点时,徐先生说要吃安眠药睡觉了,果然不到五分钟,徐先生已发出轻柔的鼾声。到第二天早上,当我七点左右醒来时,徐先生已散步回来,等我一起去用早餐。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午饭之后,我与徐先生一起回到房间,他关照我放心睡午觉,他看报,到时会叫醒我。原来徐先生还不睡午觉!我的“照顾”身份彻底崩塌,到底是谁照顾谁?这次会上我唯一起到“照顾”作用的是会后参观宜昌的三峡大坝,有一段台阶我扶了徐先生一把,恰好又给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一通赞美外,还要让她的学生以我为榜样,“看看谭老师是怎样做学生的!”真是无地自容。
作者与徐中玉先生参加大学语文年会,摄影冯文丽
另一次给我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10月在江西财经大学召开的全国大学语文第十二次年会。会议非常成功,加上主办方和中文系校友的热情接待,徐先生精神大好,非常开心。但乐极生悲,回程路上的遭遇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那天,徐先生、齐森华先生、方智范先生和我同机回沪,下午四点的飞机,我们中午还与校友在一起吃饭。去机场的路上还是顺利的,登机了也没事,但当飞机攀升时,徐先生开始呕吐,且越吐越厉害;飞机还在攀升,平常人都会有不适的感觉,何况是一个正在呕吐的耄耋老人!我们三个都非常紧张,连我素来觉得“胆大心细”的齐老师也声音颤抖。等到飞机平稳时,徐先生又感觉肚子难受,我和方老师赶紧左右搀扶他到厕所,我把着厕所的门不敢关闭。两小时的行程这样的上吐下泻有两次。快到上海了,我跟他商量,我们直接去医院,并建议就近到长宁区中心医院,这时的徐先生已经立不起来,但思路非常清晰,真是临危不乱:“不,直接去华东医院!”后来据华东医院的医生说,徐先生当时的血压已很低,是很危险的。第二天,我们再去华东医院探视时,徐先生已经脱离危险。这时徐先生的长子徐隆先生也来了,看着病床上虚弱的父亲,再看看我们,没有抱怨,只是幽幽地说了一句:“我六十多一点就退休了,老爷子九十多了还在工作。”我知道,这是说给我听的,因为那时我是系主任。
三、“跟”徐先生编杂志
在国内中文学科中,华东师大中文系有多个指标排名第一,且很难超越。一是长寿,我们是海内外闻名的“长寿系”;二是主办的杂志在国内高校中文学科中最多;三是民政部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我们有三个。这三个指标都与徐先生相关,就长寿而言,徐先生享年105岁,我们系里的老师至今尚无人超越;中文系主办的7个学术杂志中有三种是徐先生创办的,即《文艺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后改为《现代中文学刊》)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而三个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也都由徐先生一手创办。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指标也可能是全国第一,即最高寿的杂志主编,徐先生从《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岗位上退下来是2011年,时年96周岁。
切莫以为徐先生是一个“挂名”主编,他是我见到的最勤勉、最投入的杂志主编,没有之一。我大致从2005年左右开始参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编辑工作,2007年担任杂志副主编,2011年与方克强先生一起接任主编。所以我“跟”徐先生编了七年左右的杂志,而这也是徐先生晚年最为投入的一项工作。何以见得徐先生编杂志的勤勉和投入呢?有几件事可以说明问题——
《文艺理论研究》自创办起一直是人员匮乏,所有编辑都是兼职。虽然明面上有编辑部,也有一批包括副主编在内的编委,但实际参与的工作并不多,主要是徐先生带着一个编务在工作。记得2007年底,我担任系主任后亟待办理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文艺理论研究》争取经费和人员支持。我在校长办公会上的陈述打的是悲情牌,所举的就是“一老一少”在编一个国家级重要刊物,这里“一老”是徐先生,“一少”指的是编务陈佳鸣。曾经不止一次有校外专家问我,徐先生这么大年纪主编《文艺理论研究》,是真的在编吗?我说是真真切切地在编,每一期刊物的最后定稿是徐先生,栏目设置是徐先生,甚至每一期的目录都是徐先生确认,而且他还习惯于把每期的目录定好后自己在稿纸上亲笔誊抄一遍,再让编务去复印发给副主编。可惜,徐先生亲笔誊抄的目录我没有保留下来,否则倒是极好的文物了。还不知编辑部是否有留存?
2007年,我与方克强担任副主编,我们一致认为要为徐先生减负,提出的方案是一审删除明显不能用的稿子,二审基本确认用稿范围,再把可用稿和拟用稿推荐给徐先生最后审定。这样做是为了大幅减少徐先生的看稿数量,但徐先生是否能接受我们心中没底,带着忐忑的心情我们跟徐先生去谈,没想到徐先生爽快地接受了。欣喜之余我们抓紧操作,但令人沮丧的是徐先生对我们的减负方案仅仅维持了一期,下一期他就反悔了。平时每一期都要看大量稿子的徐先生怎能仅看区区三十多篇我们审定的稿件呢?我猜想当时与他谈时,他其实没有完全理解,等拿到薄薄的一包稿件时,他才发现“上当”,而马上反悔又不好意思。于是一切恢复到常态,这一恢复又持续了三年多。
到了2010年底,徐先生在与我聊天时经常有意无意地提到不再编杂志的想法,我采取姑妄听之的方法不接他的话头。到来年,徐先生跟我聊引退话题的频率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先生招我去他家里,用“告知”的方式宣布不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理由是近期每每忘事,且越来越厉害。先生最后几年已不能辨来人,或许这是先兆?我不知如何应对,只是说希望徐先生、钱先生还带着我们,具体事情我们做,但刊物主编不换。徐先生笑了,露出一种不再“上当”的神态,声称我当顾问,还是压着你们啊!
如今我当主编(先后与方克强和朱国华先生合作)也已快十年了,我常自省,与徐先生相比我做了些什么呢?真是惭愧得很呐!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
2019笔会文粹《这无畏的行旅》